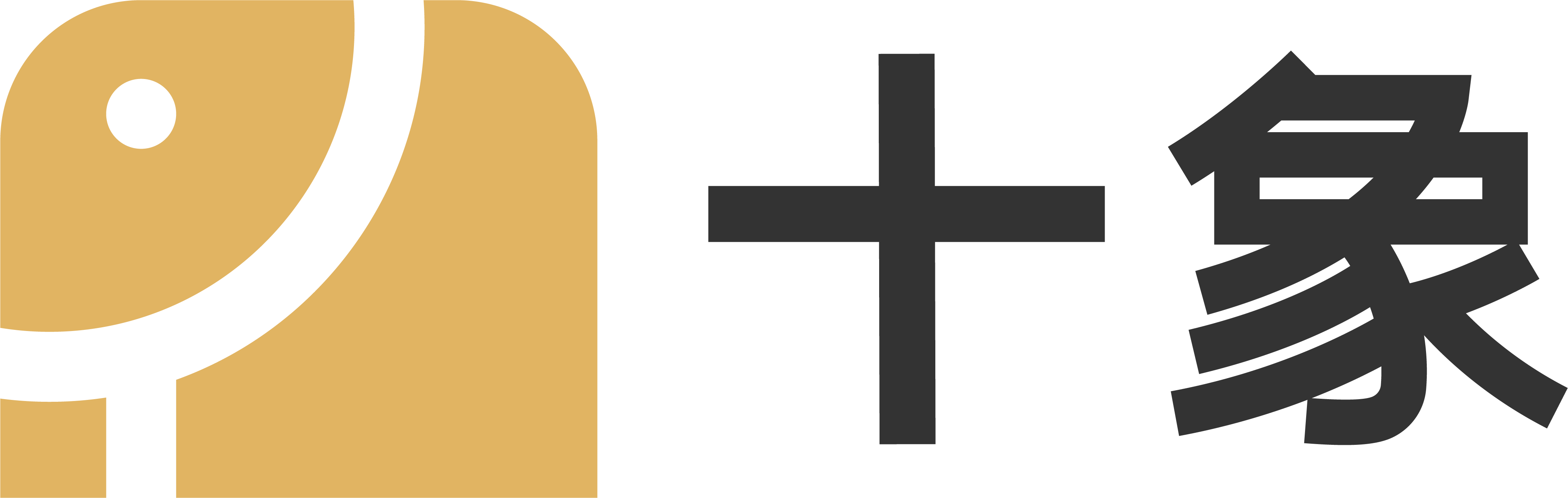他們,在冬奧會前上場
- 作者: 商標實時新聞 發布時間:2024-01-12 18:02:33
- 摘要
張嘉豪在學會“落葉飄”的那個冬天,愛上了滑雪。“落葉飄”是單板滑雪的基本功,學好了,可以像落葉從高空飄落那樣,呈Z字型在雪道上左右擺動著滑行。那一年他17歲,被就讀的職高打發到凱賓斯基酒店做學徒,在不
原標題:他們在冬奧會前上場
張嘉豪在學會“落葉飄”的那個冬天,愛上了滑雪。“落葉飄”是單板滑雪的基本功,學好了,可以像落葉從高空飄落那樣,呈Z字型在雪道上左右擺動著滑行。

那一年他17歲,被就讀的職高打發到凱賓斯基酒店做學徒,在不同的部門實習——日本餐廳、西餅房、肉房、意大利餐廳。每日,他拿著固定的配方表執行任務,做便當、烤土司、切肉、灌香腸。
他用擠出的時間滑雪。滑雪的時候,雙腳踩在這寬約30厘米,長約1.5米的雪板上,手臂、肩膀、腳跟,身體的任何輕微變化,都會牽動全身,讓人停住、變速或轉向。他覺得,這項運動教人產生“自由”“飛翔”的感覺。
他遇上的是中國滑雪市場開始“爆發式增長”的時代,2015年,北京成功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。申奧成功當年,滑雪市場規模增長近百億元,全國多了108家滑雪場、700臺造雪機,魔毯總長度增長了兩萬多米。
那時有一群人因愛上滑雪碰見,年齡職業各異,張嘉豪是其中最小的一個。
2016年,在鳥巢舉辦的沸雪北京世界單板滑雪賽上,張嘉豪拿到了當時的全國最好成績。處于運動生涯巔峰的他想去冬奧會沖一把,站到這個“最高榮譽”的賽場。
聽到張嘉豪的這個愿望,他的朋友,滑雪愛好者劉晶磊“始終覺得這事兒不太靠譜”。另一位朋友——職業滑雪教練大國覺得“希望不大”,并且他相信,張嘉豪自己也明白這點。而張嘉豪父親想到,“在咱們的概念里,參加奧運會是不是必須得是國家隊的啊?”
但一起滑雪的朋友都知道,張嘉豪是雪場上最“瘋”最“愣”的一個。2021年8月起,張嘉豪頂著疫情在全球刷比賽,參賽經歷和名次將為他贏得積分。按照國際雪聯的要求,作為東道主國家選手,世界杯前30的比賽成績和本國排名最高的積分,可以換得冬奧會的入場券。
失敗在111天后到來。在荷蘭的兩場比賽上,他出現相似的失誤,落地沒能站穩,止步洲際杯預賽,沒能進入世界杯賽。
在冬奧會倒計時48天的時候,張嘉豪對劉晶磊說,“我運動員的路走到頭了。”他扎進雪場的這些年,中國滑雪大環境在變。如今,中國滑雪市場規模接近900億元,5年內翻了一番。更多的年輕人涌了上來,目前在國內同項目運動員里,張嘉豪已經從排名前三變為排名前十。他已經26歲,到了該退役的年齡。朋友們也從滑雪轉向教學和幕后。屬于張嘉豪和他朋友們的單板滑雪時代,已經過去。
失敗
張嘉豪記得,2019年后,他已經沒有那么多“想贏”的欲望了。他知道贏不了。2016年到2019年,他在國內比賽中能穩定拿到前三名,還在坡面障礙賽中獲過全國冠軍。5年前,國家單板大跳臺和坡面障礙技巧國家隊成立。他有過進國家隊的想法,但當時的他已過20歲,那邊回復說,“你先自己練著,我們需要了你再來。”
劉晶磊看到張嘉豪在一步步落后。“就在眼前發生,也不用解釋,大家都看得明白。一次次比賽,那些人成績嘩啦嘩啦的,進步太快了。”
但張嘉豪“說白了還是有點不服,想再拼一把”。于是,2021年8月,張嘉豪只身前往美國、加拿大、智利、瑞士、荷蘭參加各地滑雪比賽,積累國際雪聯積分,沖擊冬奧會資格。4個月里,他一個人處理衣食住行的瑣事。顧不上考慮營養問題,“有什么吃什么”,在高強度的比賽間隙,他有時候會吃泡面。
疫情正在全球肆虐,不斷變換的確診數字,不斷取消的比賽和簽證,給他增加著不確定性。張嘉豪出發前想過此行最壞的結果:“感染新冠”。
從智利去瑞士時,比賽前一星期他的簽證才在中國辦好,快遞來不及,他說讓朋友去機場堵,找最近的一趟航班上的陌生人,幫忙帶護照過去。他幾乎每次比賽“都是卡哨,全部是命懸一線”“能夠順利出發都已經是萬幸。”
11月19日,劉晶磊接連接到從荷蘭打來的電話,中間相隔不到一小時。電話里,張嘉豪說剛剛那一輪“沒站”(滑雪術語,指做完空中動作后成功落地——記者注),但是他腦子里清晰。
以往,電話會間隔1到2天才打來。劉晶磊感覺到了“不對勁”。他在電話里說,“你就感覺跟我比賽,上面站著我、大國、小虎,你可別當回事,就想著咱在喬波比呢。”但是,在最后一個外轉720度加內轉900度,張嘉豪還是沒有控制好平衡,摔在了地上。他的冬奧會之路結束了。
父親是從廣東打來的流調電話里,知道張嘉豪已經回國隔離了。而他發微信去問,張嘉豪過了很久回復說,“剛到瑞典,累著呢”。荷蘭比賽失利后,他曾對兒子說,瑞典還有一場比賽,要不要再去沖一把?父親覺得,他在“掩飾”自己的失落。
張嘉豪在滑雪上傾注了所有。他沒有錢。過去在面包房的實習工資,一個月1200元。父親做廚師的收入支撐全家,他和父親、奶奶住在一套兩居室里,直到26歲,都沒有自己的房間。他沒有時間。面包房的工作經常上夜班,一晚上要用完12袋面粉,做幾千個面包。起初他只有一套雪服,每天都穿,幾乎不洗,在去雪場的車上,朋友常會開著窗戶,即使這樣,還是能聞到一股汗液發酵出的酸臭。他甚至不夠有運動天賦,朋友跳幾次就能做成的動作,他要跳十幾次,“靠數量堆”。
滑雪在當時完全是小眾運動。職業滑雪教練大國說,現在的滑雪圈變得魚龍混雜,而9年前,滑雪與名利毫無關系,全國職業滑手中能拿到商業贊助資金的只有2個,更沒什么熱度。當張嘉豪19歲決定從面包房辭職時,滑雪帶來的收入,諸如比賽獎金,一年也不足1萬元。因為辭職的事,父子倆鬧了半年不愉快,父親的想法是,“這東西只能當愛好。”
事實上,那正是當時滑雪圈多數人的狀態,他們靠主業養著這個心頭好,未掙來一分錢。
幾個月前,被一個滑雪圈自媒體采訪后,張嘉豪的抖音賬號突然漲了20萬粉絲,涌進兩萬多條私信。在紀錄片《滑雪瘋子》底下,人們寫下幾百字的評論。很多感想與體育無關:“社畜看了有點想哭。”“如果閑下來我什么都不想做,我沒有熱愛沒有欲望,我想,我是不是就是世界運轉的小小字符,在我不需要為整個體系運作而工作的時候,就安靜呆在那個小格子里。”“能有一個渴望進入的考場已經很讓人羨慕了。”一條評論有1942條點贊:“如果不是看到這個視頻,我都意識不到我已經對生活麻木了。看了這個,突然感覺神經觸動了,我才26,人生還有無限可能啊。”
但如今,張嘉豪必須承認,他的一些可能失去了。
瘋子
張嘉豪也說不清滑雪哪一點迷人,但他就是愛了。每次來到雪場,張嘉豪和平日像兩個人。他顧不上和人說話,心思全在雪上。雪地不像水泥地,每一天、每一小時都不同。早晨的跳臺結層細冰,上午最好,到了下午1點,跳臺會被磨損得有些變形。有時滑行速度快,雪板在雪地上揚起雪花,打在臉上,涼涼的。
發小戎戈濤是在2012年突然接到張嘉豪電話,“我們滑雪去”。那時,張嘉豪剛剛滑了三四次,學會了后刃推坡,能在山上做“落葉飄”了。戎戈濤也很快愛上了這項運動,覺得刺激、有成就感。
張嘉豪攛掇戎戈濤來他的面包房工作。這樣,兩人可以一起上夜班,在下班后去滑雪。晚上在揉面、烤面包的時候,張嘉豪會和戎戈濤討論技術,但很快,張嘉豪聊的東西他聽不懂了,“他進步比較快”。他們一度不知疲倦,走著路都會不自覺地突然轉體,每天只用在路上的3小時來睡覺。有一天張嘉豪去冷凍庫取貨,過了40分鐘才回來——他躺在冷凍庫門口的面袋上睡著了。他們每天早晨7點半下班。沒有錢打車,乘公交車從亮馬橋出發,到站后換大巴去雪場。大巴每天早上8點15分發車,早高峰時的三環常堵車,公交到站時,常常就已8點10分。這里距離大巴發車地點還有一公里,追滑雪大巴成了兩人的日常。跑下公交車,抱著滑雪板,開始沖刺。
這個過程中,戎戈濤曾不小心把張嘉豪的滑雪板磕到了路沿上,沒怎么破損,還是被他罵了半年。那是張嘉豪第一塊滑雪板,攢了大半年的錢買下的。
張嘉豪攢錢的方式是盡量少地在外吃飯。奶奶回憶,那時他早晨出門前,會去慶豐包子鋪,用老年卡大吃一頓,吃9個包子、1碗炒肝、1個雞蛋。去滑雪場滑一整天,不吃飯,晚上回家再大吃一頓。奶奶記得他回來時總是很餓,能吃兩塊牛排、一整張披薩。
張嘉豪沒有車,一起在外地滑雪,他會在早晨7點把有車的人叫醒。他甚至改變了大國的作息,變得早睡早起。別人去雪場滑3小時就歇一歇,他要從雪場開門滑到關門。大國甚至嘲笑他,“這人不有病嗎?”
很多人都在為滑雪吃苦,有朋友在雪場受了傷回家也不敢說。
張嘉豪是朋友中受傷最多的。剛開始滑雪時常鼻青臉腫地回家,嘴有時因為磕破而撅著。除去這些小傷,他雙手、右腿都骨折過,至少有過3次腦震蕩,還曾在一次摔倒后咳血,被診斷肺部破裂10%。如今他的臉上也依稀可見疤痕,那是落地的時候,雪鏡把臉磕傷了。
雙手骨折時,他兩只手都打著石膏,吃飯都需要人喂。但沒到一星期,他就央求戎戈濤帶他一起去雪場,起初說好了不會飛跳臺,只是滑普通雪道,但到了雪場,戎戈濤幫他套好雪板和雪服,再去自己穿雪板,一抬頭他就不見了。過了一會,戎戈濤聽說,“那邊有個人打著石膏抻著手在后空翻呢。”
9年里,他唯一間斷滑雪的時候,是右腿骨折時。那個月他每天晚上喝酒,喝完酒睡一覺,白天又去室內訓練。“雪上的狀態是由雪下決定的。”他要提升肌肉力量,做些基礎練習。不能用腿彈跳,他靠后背的力量來練蹦床。
張嘉豪用過的十幾塊滑雪板在家里各處散落著。他滑雪勤,有贊助商贈送裝備后,他平均半年要更換一塊。滑過的道具在雪板的背面留下道道劃痕。
劉晶磊總說,“滑雪改變了他的一生。”如果不是愛上滑雪,張嘉豪應該還在凱賓斯基地下室里的面包房里,看著那套來自歐洲的經典配方表,重復制作相同的面包。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高鐵,坐飛機,第一次出國,都跟滑雪有關。
過去他學習很差,在班級里是不被喜歡的學生,“再不好好學習就變成張嘉豪那樣”。初中時他在英語答題卡上畫畫,只能得20多分。中考前,為了不影響整體升學率,他被老師勸說報考職高,不參加中考。第一次去新西蘭滑雪時,他連“中國”的英文單詞都不會拼,只寫出一個“C”,被朋友嘲笑說是“C國”的。而如今,為了比賽,他獨自走過歐洲、南美,能把偶像——加拿大滑雪名將MaxPorrot的名字念得標準,他手機上安裝了背單詞的軟件,每天睡前背一背。
朋友
張嘉豪和他的朋友們趕上了中國滑雪運動快速發展的那些年。他剛接觸滑雪的時候,常去的是喬波室內滑雪館或南山滑雪場,他和朋友們在那里相識。說的第一句話總是:“你這個動作是怎么做的?這個腿要怎么著?”當時的喬波滑雪場同時會有幾十個人,但真正在認真練習、玩跳臺的,只有那么十幾個,“時間長了,發現人都是固定的”,能夠認清彼此的臉。見了面,他們擊掌、碰拳。
當時的雪場雖有教練,但技術還不如他們。回想起那幾年,劉晶磊覺得,那是多單純的熱愛,“恨不得要走在整個行業前面”。
跳臺滑雪需要先做蹦床訓練,他們那時甚至連這一點都不知道,硬生生地直接跳。后來,張嘉豪曾和一位長他近20歲的滑雪愛好者張富成一起去北京體育大學和國家跳水中心蹭設施。張富成認識一個在跳水中心安裝蹦床的師傅,以維護蹦床為名義,偷偷跟著師傅進去,跟著那些國家隊運動員一起練。有人問他們是誰,張富成就說,我們是來測試蹦床,看好的話就買了。張富成覺得,“差不多就得了”,但張嘉豪很楞,一直蹦,不下來,“把奧運冠軍都擠走了”。
再后來,包括他倆在內的6個人湊了3000多元,買下一個圓形、直徑3米的小蹦床。放在一個網球館的角落,讓網球館的保安老頭幫忙打點。那幾年,每天還沒起床,張富成就會收到張嘉豪的信息,“張叔,蹦床去?”
2015年后,北京的室內蹦床館愈加成熟,他們有了更正規、成熟的訓練設備,就不再去網球館蹦床。后來,幫他們給蹦床掃灰塵的保安得了癌癥去世,他們去了就傷心,再后來,那個“承載著青春”的小蹦床也丟失不見了。
從2003年開始滑雪,張富成目睹了中國單板滑雪20年的歷程,他感慨,如今,這項運動的規律已經被掌握,訓練更科學合理。他們曾經靠一腔孤勇,硬摔。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過腦震蕩的經歷。這是從高空摔倒后腦袋著地造成的沖擊,使人短暫失憶。在那時的滑雪場,常能看到有暈暈乎乎的人,不停地問別人“我是怎么摔的”“我是怎么來的”。
這些事讓人后怕。有位愛“刷雪道”的老朋友,比張富成還大幾歲。五年前,在雪季要結束的前一天,沒有剎住車,從雪道撞到了大樹上,至今癱瘓在床。更多朋友,因為受傷影響了工作和家庭關系,最后放棄了滑雪。
張富成是個職業經理人,工作時間自由,雪季常能保持一周五天的訓練強度。非雪季,也會把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輔助訓練上。他和張嘉豪一樣刻苦,但由于年齡原因,總不能那么靈活。在參加比賽時,主辦方老發給他“年齡最大獎”,他不高興。因為覺得“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資本”,而且他對滑雪本身“有要求”。得了獎那天,他回看自己比賽視頻,發現自己動作非常難看,不優美,一夜沒睡著。他知道自己年齡大,不能受傷,訓練起來尤其謹慎。有一個動作,他等了8年,在蹦床上練習了多次,盼望著能在去年冬天做出來。但由于疫情,沒能成功,雪季又來了,這次他希望能夠實現。“人生能有幾個8年?”
滑雪幾年后,戎戈濤也和張嘉豪一樣離開了面包房,輾轉做了滑雪、蹦床館教練后,他迷上了壓雪車司機的工作。這項工作技術性很高,在國內缺乏相關人才,他要自費去學。如今他在崇禮的山里工作,幾個月才能回趟北京,他喜歡這樣的寂靜。夜間工作,常有松鼠、狐貍被壓雪車的燈光吸引,蹦到他眼前。他會看到造雪,幾個特別大的雪炮立著,炮口是一堆花灑,水打得特別細,往一個風速特別大的一個風扇那噴。當溫度夠低,小水珠吹出去,在空中就變成雪,飄下來。
造雪完成后,他要先把雪鋪開,鋪成雪道,再在雪道上繼續造雪,然后在上面塑形,做大的跳臺、道具底座。這是戎戈濤從小到大,最感興趣的一件事。跳臺和道具的設計沒有統一標準,有創造性在里面。“如果自己有一天做了自己的公園(指跳臺滑雪場),自己去玩,也讓大家去玩。”這份工作居于幕后,認知度很低。有親戚覺得他這工作沒有前景,叫他去跟著他們干保險業務,他拒絕了。
今年冬奧會,他將參與比賽中跳臺的制作。
新星
9年過去了,在現役滑雪運動員圈子里,張嘉豪從年齡最小的,變成年齡最大的。滑雪場里,他看著長大的蘇翊鳴和谷愛凌到了作為運動員最好的年齡。
這個冬天,17歲的蘇翊鳴成為世界上首個完成內轉轉體1980度的人,收獲中國首個單板滑雪大跳臺世界杯冠軍。1月2日凌晨結束的單板滑雪坡面障礙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爾加里站,蘇翊鳴首秀獲得第六名,在微博上宣布他拿到了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比賽資格。
同樣在1月2日的加拿大卡爾加里,2021/2022國際雪聯自由式滑雪U型場地世界杯上,18歲的谷愛凌獲得冠軍。當天大風,沙塵一般的雪花飛揚著。在U型池中,她旋轉、跳躍、滑行,在宣布成績時開心地大喊起來。
2021年12月28日,有媒體評選“2022年中國體育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新星”,他們分列第一和第二。而9年前,他們被滑雪場里的人叫作“小鳴”“愛凌兒”。
這幾年,張嘉豪的一頭板寸留成了卷曲的長發,他常戴著棒球帽,摘掉時,能看到頭發被扁扁壓出球型。童年照片里,他皮膚白皙,滑雪場的紫外線加深了他的膚色,在一張去新西蘭滑雪拍攝的照片里,他的臉上甚至有一道雪鏡留下的黑白分界線。
他沒有在童年接觸滑雪,沒有接受系統的訓練,沒有進入國家隊,在技術上他遠遠落后于那些“小朋友”。
如今,張嘉豪發現自己運動后,體力恢復得更慢了。最近的電話里,他總問劉晶磊,“你覺得我泄氣了嗎?”劉晶磊說,就像十幾歲的小孩不會問自己是否老了一樣,張嘉豪之所以問,是因為一些東西確實改變了。
冬奧會
最近一年多,張嘉豪對朋友談起錢的時候更多,也學會了應對媒體。最近半年,他擁有了個人商務團隊,微博不完全由自己運營。他的日程表上排滿了媒體采訪。12月26日這天,他在冬奧之旅后首次回到北京,穿著一件印著“中國”字樣的衛衣坐在錄影棚里,被6個工作人員、3塊高大的反光板圍住,看起來有些疲憊。3個媒體的記者一同見了他,之后,他休息了半個多小時,就又開始了新的視頻連線。在沒有暖氣和空調的錄影棚里,為了不露出衣服商標,他穿著一件白色單衣,在對著鏡頭露出拘謹靦腆的微笑。
他反復說著“自洽很重要”,有媒體記者甚至覺得他“很多官話”。但這就是他應對“工作”的方法。在攝像機關掉后,他語速變快了,身體變得好動,和在場的記者碰拳,說想“趕緊完活兒,滑雪去”。
26歲是該考慮現實問題的時候了,“他也必須把這當工作”,劉晶磊說。他變得沉穩。從前,他拒絕添加父親微信,后來加了微信,但將朋友圈對父親隱藏起來。而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,父親發現可以看見他的全部朋友圈了。他曾經討厭學校和課堂,如今他成為北京體育大學大一新生,把朋友圈背景設置為解剖課作業,作業上工整地寫著學號。以前,面對奶奶的催促,他說到了30歲再找對象,但最近,他總說讓朋友給他介紹女孩。
變化在所有人生命中發生著。劉晶磊快要40歲了,他想,如果以后的孩子要折騰、要理想,他還是會阻攔,因為他明白那“不現實”,會受傷、浪費時間。但回想起滑雪的10年,想到的卻是高光的瞬間,他想到大約6年前,他做的動作一度在全國領先。10年來,他還是為了生計做著一份廣告制作的工作,滑雪沒有給他帶來名利,但是“構成了我人生一份完整的故事”。“自己追求過的人都會發現,不會后悔。”“當你站到山頂的時候,所有的痛苦你還是會忘記。”
如果不是滑雪,他就不會去那些人跡罕至的高山,不會體會到滑著雪穿越云層的感覺。為了滑雪,他們在全球追逐雪季,新西蘭、阿拉斯加、日本。“如果你沒有這個愛好,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地方的冬季。”他也懂得了冬天的殘忍,車被陷在深深雪坑里,礦泉水不一會就凍成冰。每年3月初,當雪季在北半球過去時,他會松一口氣:這個雪季平安度過了。
回想從前,劉晶磊會“覺得自己太小了,不成熟,挺傻的。但你說那會兒快樂嗎?肯定快樂,但是現在快樂嗎?不快樂。”
大國懷念9年前滑雪圈的“人情世故”,當時,大家一心想的是“玩得更牛,更厲害”,一塊鉆研。而如今的滑雪圈人多,混雜著許多只是“想當網紅”的人。他結了婚,有了孩子,成了一名職業滑雪教練。工作與滑雪有關,但卻“只是為了賺錢”,“每天都是雞毛蒜皮”,操心的是孩子們的安全,如何安排場地,如何讓他們進步。
張富成也想,那個時候他摔倒之后,腦子暈乎乎,什么事都不記得,跟別人重復地打招呼,“但還是覺得那時候好。”2015年后,一切都在爆發式增長。起初,這個圈子的人他能認全,但現在,手機里的滑雪群越來越多。“季卡群”“年卡群”,以至于有群再拉他,他不再想進。
劉晶磊很懷念2012-2014,他們滑雪的最初兩年。他想回到他們十幾個人站在南山滑雪場跳臺的出發臺上那個瞬間。那時候,沒有商業贊助,沒有教練,沒有科學的訓練方法,沒有冬奧會。沒有人想到滑雪能當做職業,能帶來什么。他們會猜拳決定誰先跳,而張嘉豪總是其中膽子最大的那個。
冬奧會之旅宣告失敗后,在接受媒體采訪時,張嘉豪被問到之后的計劃,他說,在考慮申請做冬奧會的試滑員。在比賽開始前,試滑員會通過自己的身體測試場館。那是一項光榮的工作,在比賽中率先出場。當試滑運動員滑過那條不足百米的、雪白的奧運賽道后,比賽馬上開始。
(中國青年報郭玉潔)